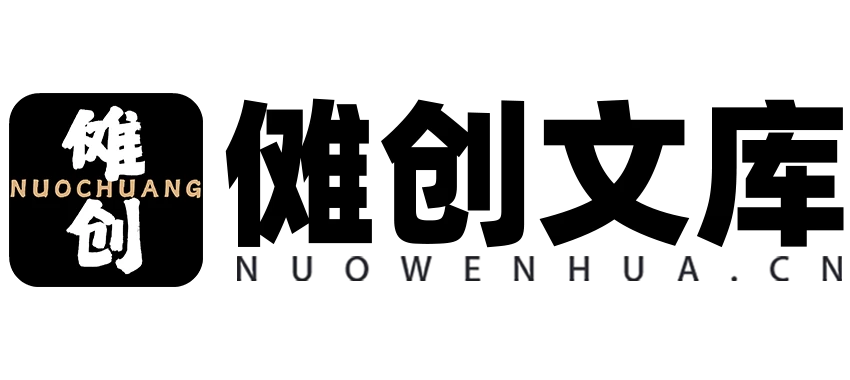摘要:“开山莽将”作为黔北地区土家族、汉族、苗族的傩堂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傩堂戏面具造型中最具代表性面具之一。分析其渊源、造型构成,及其民族文化身份隐喻,皆指涉出该区域民族文化形象与民族艺术高度结合与浓缩的体现。
关键词:贵州、傩堂戏、开山莽将、民族文化形象
一、“开山莽将”研究之意义
傩堂戏主要流行于黔东、黔北、黔南、黔西北等地土家族、汉族、苗族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研究者习惯将黔北傩堂戏与土家族对等,这是极为狭隘的研究。傩堂戏同样流行于该地区的汉族与苗族间,从目前考察傩堂戏面具实物看来,已被证实。从研究角度而言,不应将其局限于具体某地或某族别,应将其定性为区域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共性特征讨论。关于该地方戏曲的基本介绍与研究,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三十年中,相关研究著述颇多,在此不再敷述。本文而着重强调对“开山莽将”这一角色的研究,这并非刻意人为夸大其意义价值,而是该区域文化内在性要求与民族艺术具体外化体现。
开山,在汉语中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事物初创阶段;佛教用语,在没有寺庙的山上开建寺院,后喻指开创一种行业或流派,开创者,或首次主持;开垦荒山等。“开山莽将”也成开山猛将,或开山、山王(山神)。从命名角度考证,其义不言自明。黔北民族对其角色的命名寄予了理想化的共同文化想象,有着美好寓意与象征的隐喻性。“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没三分银”,这是对贵州自然山地地貌气候特征的描述,当然这也极大的限制了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民族内部迫切希望发展,或祈求降临一位能对其生活带来实质方便与改善的神祗,自此“开山莽将”则应运而生,符合了其民族内外逻辑。“开山莽将”(或猛将),从字意理解,可将其武将或猛将对等,这体现出传统农耕社会,冷兵器时代,乃至更早的史前人类,对来自肉身力量的崇敬与迷信,对生存与生命最为质朴直接的认知。
本文之所以将“开山莽将”这一角色作为黔北傩堂戏乃至该区域民族文化形象的代表来进行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虑。从造型角度而言,该角色形象充满想象,虽狰狞夸张,但不失质朴,有异性同构的造型特征,予人一种崇高美的审美感受,这一形象的独创性,体现出该区域民族文化独特的审美特征;从角色功能的角度而言,其驱邪纳吉的正神身份,体现出该区域民族美好的文化想象,予人安稳、踏实,保得一方安宁的内心感受;从宗教信仰角度而言,该形象体现出巫傩与道教融合的典型性,有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代表性;从地域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地方政府有意识地强化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使其成为该地区巫傩文化的文化符号代表,而该角色也极好的体现出了巫傩文化神秘、夸张、驱邪纳吉的文化本质特征。综上所述,将其单独展开研究讨论,对于区域民族文化理解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二、“开山莽将”身份之谜
关于“开山莽将”的身份有多种解释。有传言“开山莽将”是蚩尤麾下的一员大将,英勇善战,屡建奇功,但是关于蚩尤大将的说法,也无从考证,可能多是对其苗文化溯源或夜郎文化的一种追加比附。此外,传说他还是盘古王化身五猖,又称五路猖神、五猖兵马。而这种说法也不具备推理性,据德江傩文化传承人王国华介绍,在其所绘的不论是三清画案或桥案中,均有五猖形象,被称之为“倒走五猖”,其人物形象一贯以双手倒走支撑身体,尽管其职能与“开山莽将”几乎一致,但显然两者并非同一形象。
贵州著名傩文化研究者顾朴光介绍,按“开山莽将”造型特征区分有正神与凶神之说法,所谓正神则是善良正直的,而凶神则是勇猛凶悍夸张的。而“开山莽将”一般安排在下半坛出场,属“凶神”系列,并排于押兵先师、龙王、灵官、钟馗等。顾朴光认为,“开山莽将”是桃源洞中一员镇妖猛将,相传他身高一丈二尺,头上长着一对红色的角,一顿饭能吃下一只整牛,行走起来山摇地动。同时,他还手执金光钺斧,专门砍杀五方邪魔,他相貌虽然凶恶,但一贯扶弱惩强,曾为百姓扫除三头八臂的妖怪。
在学者李渝看来,“开山莽将”与远古神话有着渊源关系,甚至认为高于“水神”为代表的二郎神角色地位 ,一度还影响到了日本。其推论依据来源于两点:一是在黔北傩堂戏《鸡毛打铁》中开山的开场自述中提到,“吾是盘古山化身”;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岑家悟写的《图腾艺术史》中关于‘盘古氏’的插图,他运用了头上长角的“开山莽将”神祗,而该神与传统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有着密切关系。自此,他推断傩堂戏中的山王(“开山莽将”)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演变过程,即由烛龙→盘古神→山王的过程。再进一步详细推演过程中则经历了:极光(自然崇拜)→烛龙(钟山山神)→盘古神(印度佛教开辟神的引入)→傩舞之盘古神(开天辟地神)→傩戏之“开山莽将”(砍五方精怪、追回人的魂魄之神)。与顾朴光观点不同的是,李渝先生从角色功能的角度将其归为“正神”系列,且判断其造型明显受到佛教“金刚药王”造型的影响。
总而言之,研究者们对其身份以及来源截止至目前仍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论证,对其身份和来源详尽的史料佐证也不完整,即便有个别介绍也没有引文出处,从而对考证该角色无形中提出了诸多困难。
三、狰狞夸张而原始质朴的造型美
在对“开山莽将”面具的制作上,民间有完整的造型口诀。德江傩面具制作传承人黎世宏在面具制作过程中遵循的是“火焰眉毛圆眼睁,来在傩堂砍五瘟;一对肉角顶头上,獠牙血口凶猛神。”而枫香溪镇王国华在面具制作过程中则遵循“下面三寸三,上面三寸三;中间五五等(五公分半),两边一样宽。”前者从具体细节构成的角度确定了角色特征,后者则从对称均衡的角度整体把握形象塑造,但最终呈现出的总体形象是较为相近的。
上文介绍,其身高一丈二,手执金光钺斧,一顿饭能吃一头整牛,行走起来山摇地动。被描述为“开山猛将生得恶,一对獠牙一对角;开山牙齿颠倒颠,晒干牛皮嚼九斤;一顿要吃三斗三升炒谷米,八十斤肥羊囫囵吞;嚼骨犹如吃炒豆,只见肋骨两边分;檬子树上去擦痒,皂角树上去安身;有脚行去三千里,反身转来关大门…”。在傩坛中,除了专门砍杀东南西北中五方鬼怪、十方邪恶,为各路神祗开路,“开山莽将”还充当净扫傩坛的猛神职责,此外还肩负驱邪收妖、追回失落灵魂之重任。为此,请傩的主人,若家中有病人,则需增加开山追魂环节,以达到对愿主冲傩的慰籍。其整体造型怪诞,神采生动,线条奔放,且充满力度。具体造型上,头长对角、嘴吐獠牙、眉毛倒竖(或火焰眉)、眼珠暴突,以直立的双角和狰狞的獠牙突出其威猛,以炯炯有神的双眼和烈焰般的眉毛刻划其嫉恶如仇的性格。其造型夸张且不失质朴,符号运用的高度概括,甚至呈现出一种抽象化的特征,其诡奇的形象与咄咄逼人的气势令人倍感恐惧,予人以勇武、凶悍、威严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暗示。对人造成的这种感受和暗示,极好的体现出其角色的身份特征。
四、面具构成之符号分析
《庄子•天地篇》中言:“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这就使道教的造像艺术不仅要明道,还要明德;不仅要反映神的神性,也要反映道教的信仰宗旨;不仅要表现其作为神的尊严,还要表现其所具有的道德,以及内在的美和它的神通。所以,道教的造像是道教德性的具体化和人格化体现。
吴承恩所著《西游记》第十四回中写道,“我那还有一篇咒儿,唤做‘定心真言’,又名‘紧箍咒儿’,你可暗暗地念熟,牢记心头,再莫泄露一人知道。”此乃观世音菩萨对唐僧的告诫,以紧箍咒对孙悟空加以控制。这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象征或隐喻,孙悟空可大闹天宫,能力自不必多言,区区一个唐僧并不能对其加以控制,然而一旦套上紧箍,则情形完全发生逆转,即谁能念出咒语,则都能对孙悟空加以控制。而在黔北傩堂戏中的“开山莽将”面具形象中,大部分面具都在其额头雕刻有类似孙悟空额头上紧箍一样的法器,目前尚且难以判断,这一符号在面具中出现是在何时。但不论如何,这种受到佛教、道教、经典文学作品影响的因素,极大的丰富了面具造型的文化内涵。
“开山莽将”作为一个区域民族文化想象的角色,其狞厉夸张的造型,令人不寒而栗,在戏剧中其降妖驱邪的身份,更是显现其法力的非同一般,然而这种法力一旦得不到约束、限制,则极有可能对百姓造成祸害。对其额头上加以一个类似“紧箍咒”的符号,一方面极好的说明其法力与能力并非任性而为不受限制,它时刻暗示在“开山莽将”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神明在监视、监督着;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开山莽将”并非是一个不受任何人或宗派管束的对象,它受到了来自神或宗教的教化,能够通人性,非等同于一般恶鬼妖怪。至此,该符号形象极好的对民众心理形成安慰,尽管其外貌恐怖可怕,但内心深处是将其封为类似神明进行供奉。
色彩的运用在面具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便是“红脸关公”,将红脸等同并列于关公,隐喻出红色所具有的典型象征意义,即正义、忠诚,与自然中的火、太阳等外在物理性产生关联,予人温暖、光明、能量之感。由目前所看到的“开山莽将”面具用色看来,其用色主色调以红色、黑色为主,其次则为黄色。从色彩美学角度分析而言,这是最为经典的配色之一。从历史考古学角度分析,我们从先秦战国时期的墓葬挖掘看来,早期大量出土的冥器或陪葬漆器便是该色调样式,从而可以看出其实该色调样式的使用历史渊源之久远。假若再加以最根溯源,我们从大量岩洞壁画中可看到史前人类对红色与黑色的偏爱。再者,从颜料获取角度而言,这两种颜色较于其他颜色易于获取,可直接从自然生活中提取运用。
红色体现出正义、光明,而黑色则体现黑暗、恐惧、邪恶。这两个主色调一阳一阴的结合,具有极强的色彩张力,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早期先民对宇宙观的二元矛盾认识,而“开山莽将”则是其认知理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