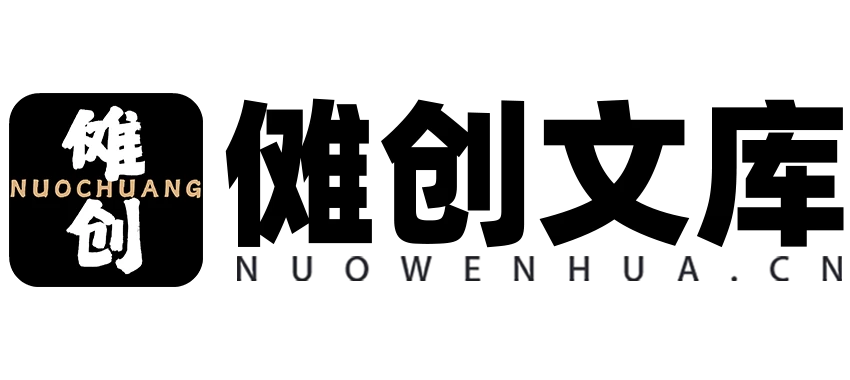傩戏面具 资料图

冷水江傩艺队的民间“巫师”苏立文。图/实习生巩玮

傩戏艺术家正在现场表演。图/摄友团谢正宇
张艺谋电影《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因傩戏而起,一个日本父亲为了身患绝症的儿子,只身前来中国云南拍摄儿子最想看的傩戏《千里走单骑》。影片中,观众在被父子亲情感动的同时,也被一种神秘的文化吸引。那黑色布面上小巧的彩色面具透着古老而诡异的气息。面具,如同神灵一般被敬畏……
傩戏,源于南方,是否源于湖南不可考。但在娄底,傩戏被保存得较为完整。
在娄底市冷水江岩口镇龙科村,说起苏立文,从耄耋老人到学语孩童,没有一个不知的,在村民的带领下,记者见到了这位68岁的老人。6岁开始接触傩戏的他,是傩戏在这个家族的第13代传承人,最近,刚刚被命名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有关傩戏]
傩戏又称傩堂戏、端公戏,是在民间祭祀仪式基础上吸取民间戏曲而形成的一种戏曲形式,广泛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省。傩戏源于远古时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既娱神又娱人的巫歌傩舞。明末清初,各种地方戏曲蓬勃兴起,傩舞吸取戏曲形式,发展成为傩堂戏、端公戏。
傩戏于康熙年间在湘西形成后,由沅水进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和艺术风格。湖南、湖北的傩堂戏吸收了花鼓戏的表演艺术,四川、贵州的傩戏吸收了花灯的艺术成分,江西、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和目连戏的养料。
傩戏是历史、民俗、民间宗教和原始戏剧的综合体,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被称为研究古代东方人体文化的活化石。包括哈佛在内的众多世界名校早在80年代,就不断派出学者来研究。目前,整个娄底懂得傩戏的艺人约有数千,政府还在继续挖掘,希望能找出更多的传人。
一唱起傩戏,就像换了一个人
苏立文老人瘦瘦黑黑,皮肤的褶皱里满是岁月的痕迹,乍一看,与一个普通的农村老人别无两样。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们的沟通,只能依靠书写;他也没进过学堂,除了傩戏的生僻“科本”,其他一概不知。唱起傩戏的时候,在古怪的言语和奇特的声调里,他好像换了一个人,眼睛焕发出夺目的神采。
“唱傩戏的必是‘巫师’,因为傩戏就是给人避邪祈福的。”苏立文强调,“谁家生了怪病,唱一场傩戏,病有时候就好了,其中的道理,我也说不清。”在这一带,他仍然是非常受重视的人物。特别是下半年,他几乎天天都要去镇上人家“唱戏”。“我们这里下半年就开始‘拜娘娘’,傩戏是夜里少不了的节目。”
傩戏在民间传奇颇多,请神治病,开运亨通,开天眼及上刀山、下火海皆由此而来。多年来,笼罩在傩戏之上的神秘色彩一直不曾散去,信者谓其神,疑者谓其假。
从事傩戏研究多年的李新吾老师说,其实从原始社会末期就有了傩祭的活动,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傩祭已经非常盛行。“相传孔子疏于应酬,但只要遇见乡傩队伍经过,必着绸服恭敬立于门前。”几千年来,群众得了病,不请医生诊治,而习惯请“巫师”唱傩戏。以前有种说法,“愚民有病,初不延医而延巫。”正是由于这种风气,所以傩戏在乡下,还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上刀山下火海,乡民才会信服
无论是傩祭活动还是傩戏演出,面具是傩戏中最引人注目的道具,直到现在它仍然被赋予了神秘的宗教含义。苏立文就告诉记者,在傩戏圈子里,面具就是神灵的象征和载体,如何对待面具,往往要遵守一些规矩。比如,制作面具时要先举行“开光”仪式,取用面具要举行“开箱”仪式,存放面具要举行“封箱”仪式等。以前面具的制作、使用、存放都是男人的事情,不让女人触摸或佩戴面具。男人戴上面具即表示神灵已经附体,不得随意说话和行动,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么多要求了。
佩戴面具的男人,也就是唱傩戏的巫师了。一个巫师,从六七岁开始学习,二十岁才能勉强“出道”。说到学习傩戏的过程,苏立文侃侃而谈,自己6岁那年,身为“巫师”的父亲就开始给他念“科本”了,再大一点,父亲就开始口传“密语”,这些傩戏的密语,书里头从无记载,只能靠代代相传。接下来,傩戏的动作、唱调、锣鼓道具的击打,必须样样精通。
每一个巫师在“出道”前还要经过一个严格的“仪式”,在傩文化里,被称为“过坛”。"过坛’就是在成百成千的乡民面前,表演‘上刀山’、‘下火海’。”苏立文介绍。“那刀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杀猪刀,柄柄锋利;那火堆,也绝对是熊熊大火,巫师只有在大家面前过得了刀山、下得了火海,才能赢得乡民的信服,后头才会请你做法。”“即使到现在,每一个巫师,都必须过这一关。”
收了几十个徒弟,大多半途而废
苏立文很是骄傲于自己的技艺,“在过去,想学傩戏要问师傅,问天地,在天地祖师面前卜卦,三卦皆过者方可入门,入门时还要赌咒发誓。现在不兴了,别说发誓,就是发了也没啥用处,年轻人都不记得了,也不害怕。”如今,苏立文收徒弟没有那么多礼节了,他说:“这13代以来,我家的傩戏都是父子相传,现在时代变了,不能那样了。我很早开始收徒弟,大概也教过几十个徒弟了,可是,有的成了,大多数却半途而废了,出去打工,赚大钱去了。”
好在苏立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苏业照、二儿子苏业烈都继承了他的衣钵:“现在,一般都是我跟两个儿子一起出去表演,我年龄大了,唱不动了,就是帮着敲敲锣鼓,但乡里人信我,只要我‘坐坛’,他们就放心。”
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陪在父亲身旁的二儿子苏业烈也向记者道出了傩戏的辛酸。“现在时代不同了,我是读了书,找不到工作,才回头来学傩戏的。当时都不敢出门,大家都觉得年轻人学这个很‘丑’。”如今以此为生的苏业烈终于不觉得“丑”了,只觉得太累了。“傩戏是夜里唱的,乡里人一般晚上八九点就休息了,我们却要一直从夜刚黑唱到午夜12点。”
苏业烈有两个儿子,20岁的大儿子在吉首师范念书,14岁的小儿子在冷江师范念书,他们没有接触过傩戏。“我不想让他们学这个,这个太苦了,我是没办法,我就想要他们好好念书!”苏业烈一再强调。记者说起傩戏失传的事,他回应:那就让我以后的孙子学吧,儿子不学了!
文章来源:中新网-红网 2011年08月13日 08:44